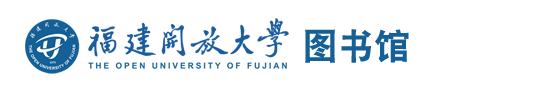《小青春》是一部有着浓厚历史记忆的成长小说。秦文君多年的文学情怀、人生热望和历史态度在这部小说中得以完整呈现,它让我们读到了一个区别于常见的儿童文学作家标签的小说家,一部区别于寻常儿童文学作品的优质小说。
秦文君将少年人物放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“文革”时期,小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得以体现——不仅对社会环境的客观书写,还提出了一个问题,如果少年需要被教育、正常的价值观需要被培育的话,那堪称悲剧的动荡年代如何承担教育少年的社会功能?怎样对抗人性之恶的流散。在这种形态下,人心的散乱和变异轻而易举。人心保持善良的动力又从何而来?
秦文君写到了成长的三个层面——生理性、心理性和社会性。秦文君写到了少年伟义的爱,纯净的、守候的、无私的感情,它的动人是内敛的,或者说是用来被怀念的。秦文君也写到少年爱情之殇。伟义喜欢的姑娘张靓,因为出身不好,家人常常遭受欺压。两人心生爱意,但这份爱在那个年代如此脆弱,挡不住外来的风暴。张靓需要一个靠山,帮她挡住风雨。少年伟义对此无能为力,张靓是现实生活给他的一计重击。
同青春期的情感相比,心理层面的成长是小说着重书写的部分。伟义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同学老巴寻回丢失的裹着“战地新歌”封皮的私密日记本。老巴没有告诉他里面写的什么,只说不管写的什么,总是可以分析出罪名来的,必须要找到。秘密日记本情节的设置,很好地串起了小说的整体性,这是训练有素的小说家所擅长的布局。有了这根贯穿始终的线索,小说就变得更为规整,情节波澜起伏。因为这根线的存在,小说空张弛有度地写到少年人的其他生活——抓蟋蟀和抢马桶等。为了得到情报,以“将军”蟋蟀换取,这符合少年人的行事逻辑。这几章抓蟋蟀的情节是小说中难得的轻松段落,诙谐风趣中有点胡闹,是印象中的少年生活,是紧张窒息的文革生活也难以压抑的少年们天真闹猛的生活。
在成长的社会性这一点,秦文君写出了让人赞叹的章节。白师傅六十大寿摆酒水请街坊们吃饭,伟义跟着妈妈去参加,受到了白师傅家人的热情招呼,白师傅是手艺人,但把最琐碎的落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。在生日宴上,找到日记本的伟义被造反分子朱刹胚抓住时,白师傅的儿媳妇挺身而出,招呼伙伴把朱刹胚堵了起来。这一几章节结构之紧凑、语言之鲜活准确、市民生活气息之浓、叙事之镜头感,显出了秦文君扎实的写作功力和独到的细节还原能力。从白师傅到他的儿媳妇的野性表达,脱离政治氛围的市民日常生活得以呈现,特别需要提出的,儿媳妇的挺身而出闪现的就是世俗伦理和价值观。加上小说中写到的许多老师,都还保存着为人师者的尊严和正直,这才是大社会背景之下的伦理小生态,少年们的意气和正直来源于此。与滚滚的时代车轮相比,这是缓慢、安静流淌的生命内河。
小伟义的成长最终完成了,恶势力的去世,秘密日记本的寻回,老巴一家的秘密也解开了。小说留给读者的余味显然不止于这些,如果说伟义的成长在于让他认识到,世界和人生有善意,值得奋斗,不要被过去和别人所困,那小说呈现出来的成长意味则更为丰富。当承担外界教育职责的社会和时代失效时,小到一个少年,大到一个社会,完成内在性格和价值观建立的工作会由谁来承担?体制的激发下的人性之恶又怎样得到遏制,像朱刹胚这样带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有毒的恶魔怎样才不会再出现,谁又能真正收拾得了他们。恶不是一个历史老问题,它永远是当下的,永远会有新的其他恶的产生,与恶的对抗没有一劳永逸的窍门。
当秦文君在伟义身上寄托正义力量的同时,她关于老巴爷爷、老巴妈妈、伟义父母以及白师傅等市民的书写和记忆,才是真的人心之善的来处,犹如微暗不绝的火种燃烧在人的心中,那才是真的希望所在。当王建生最后坦白是自己纵火犯而不是救火英雄被拉去游街时,伟义不顾车上民兵的阻拦,迅速爬上卡车,把王建生衣襟拉下来,盖住肚子,还将军帽脱下来,按在王建生的头顶上。我以为这就是人格的成长。即便在最为困苦潦倒的时候,也有一群人不肯潦倒下去,少年伟义自己耳闻目染,见证了这些,这便是成长的全部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