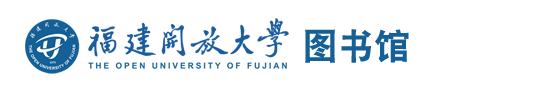在这个越来越实用主义的时代,真正沉醉于阅读的人,确乎是越来越少了。所以,台湾诗人痖弦在《寂寞》中感叹:“一队队的书籍们/从书斋里跳出来/抖一抖身上的灰尘/自己吟哦给自己听起来了。”这些“书籍”显然多是“无用”之书,故而不被青睐,只能寂寞自语。事实上,忙于阅读的人向来不少,或为升学,或为考证,或为求职,焚膏继晷,孜孜不倦,当然,也头晕脑涨、苦不堪言……像这样怀有强烈功利性的阅读,已经成为社会常态,却距离阅读的本意越来越遥远。
阅读,本来是人生一大乐事。杜威有言,读书是一种探险,如探索新大陆,如征服新土地;法朗士也说过,读书是“灵魂的壮游”,尺幅之间可见山川名胜、幽谷奇花;薄伽丘甚至说,他在书堆中,享受到了世界上“任何君王都无法感受过的无与伦比的快乐”;欧阳修则由衷地发出感慨,“至哉天下乐,终日在书案”。
那么,怎样才能从阅读中获得“至乐”呢?
李清照与赵明诚为读书人树立了一个“读乐”的范本。易安居士在《金石录》后序中生动叙述过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:“余性偶强记,每饭罢坐归来堂,烹茶指堆积书史,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,以中否决胜负,为食茶先后。中即举杯大笑,至茶倾覆怀中,反不得饮而起,甘心老是乡矣!故虽处忧患困穷,而志不屈……收藏既富,于是几案罗列,枕席狼藉,意会心谋,目往神授,乐在声色犬马之上。”享受这样的精神愉悦,需要性情相投、声息相通,更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。
林语堂认为“真正的读书”才是快乐的,“一句话说,兴味到时,拿起书本来就读,这才叫作真正的读书,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”。他还描绘了“乐读”的佳境,“或在暮春之夕,与你们的爱人,携手同行,共到野外读离骚经,或在风雪之夜,靠炉围坐,佳茗一壶,淡巴菰一盒,哲学、经济、诗文、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,然后随意所之,取而读之,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。”这样的阅读是超越了功利性的,正如蒙田晚年所言:“我读书纯粹只为自娱,不为获得什么。”
善于享受读书乐趣的人,会根据时令、环境来选择书籍,感兴于中,并由字里行间读出人世的种种乐趣。
要想享受读书的快乐,还必须善于读书。袁枚说过,“读书如吃饭,善吃者长精神,不善吃者生痴瘤。”台湾著名书人郝名义编过一本叫《阅读的狩猎》的书,把阅读比喻为狩猎,把善于读书的人比作好猎手。这本书提供了“好猎手”《修炼指南》:作为一个新手猎人,首先要避开图书排行榜的陷阱,学会去书店的角落里搜索。商业时代的图书排行榜,上榜的新书并非都是值得去读的。叔本华说起当代人爱读毫无价值的新书就充满怒火:“平凡的作者缩写的东西,像苍蝇似的,每天产出来,一般人只因为它们是油墨未干的新书而爱读之,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……其中那些每日出版的通俗读物尤为狡猾,能使人浪费宝贵的光阴,无暇读真正有益于修养的作品。”
找到目标以后,最好每个主题的书积累50本——没有读完也不要紧,至少开阔了视野。书读多了就像练习射箭,熟能生巧,天长日久自然就练出百步穿杨、张弓即中的本领。要想成为一个好猎手,还必须“不怕走错路”。走了几回歧路,就积累了识路的经验。所以阅读中不要怕读到没有价值的书,台湾著名书人唐诺就说过,“买错书应该作为阅读找书的前提”。当然,倘若买了错书,读过几页几章发现味道不对,应该当机立断弃之。
最高境界的“猎手”是不会单纯专注于阅读本身的,他还会将书本与现实结合,从而提升自己享受快感的能力。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千里路。”清代学者顾炎武就是一个典型。他用一头骡子载书,交换着骑两匹马——一边行走天涯,一边博览群书,如此二十多年乐在其中,终于写成《肇域志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以及读书笔记《日知录》。要真正读出书中的真味,更需要将人生的经验融入其中。
一个人的阅读历史,其实就是一部心灵成长史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说“如果将一个人阅读《哈姆雷特》的感受逐年记录下来,将最终汇成一部自传。”对于个人而言,“阅读史”记载着自己与书本相识、相知、相恋,直至携手终老的过程。在这个漫长的阅读过程中,阅读者时时会在书中发现新的自己,会留下一路惊喜。
阅读之乐的最高境界甚至可能与阅读本身无关。
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《摸书》的散文,讲述了一位名叫莫拉的老妇人嗜书如命的故事。莫拉对作家说:“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书里。”又说:“我收藏了4000多本书,每天晚上必须用眼扫一遍,才肯关灯睡觉。”她常常情不自禁地“摸书”,“摸一摸就很美、很满足了。”她已去世的丈夫是个“书虫”,终日待在书房里,除了读书之外,便是把那些书搬来搬去,翻三翻、看一看、摸一摸。莫拉藏书及摸书的嗜好,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丈夫的影响。她幸福地回忆,“他像醉汉泡在酒缸里,那才叫真醉了呢!”
因书而醉,这是怎样的快乐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