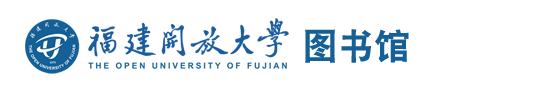关于读书,我能向比我更年轻的人们说些什么呢?我不愿再说些囊萤映雪的故事,那已成为有口无心的套话;我也不想像鲁迅那样作出“不读中国书”之类的断语,我知道向青少年作偏激语是危险的,他们往往信以为真。其实对于读书的看法从来就歧异纷纷。有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有人则说耽于读书和思考是人的堕落;历史上的许多大英雄是从来不读书的,如刘邦项羽,但也有不少伟大人物却嗜读如命,如列宁毛泽东。对于文人学者来说,读书是立身之本,常被视为胜业,所以杜甫说“读书吾家事”;不过他们之中也不乏自轻自贱者,说是“寻章摘句老雕虫”、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。究竟如何,全凭各人的慧根、缘份和信仰。我在这里所能说的只是我自己的经历和选择。
我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始读书的。我生于乡村,少时家贫,吃饭都勉强;我至今也说不清是什么契机引发了我对读书如此强烈的欲望,我没上学时就求哥哥教我识字,未及学龄就进了学校。学校离家二里多路,我因年幼甚至不能一口气走完,中间得停脚歇一歇再走。记忆中星期天必坐在屋后的树荫里看书,看着看着树荫就变成了太阳地,就再找树荫;就这样逐着树荫走,一看就是一天。有时看麦场,抱着书看得入迷了,谁家的鸡成群地啄食晾晒的粮食我也不知道,等路过的人用夸张的声音帮我赶鸡我才惶然惊醒。婶婶见我看书,总是问:“你看的是诗吧?”婶婶没文化,在她心目中诗是最了不起的;其实我是弄到什么书读什么书的,那时候能得到一本书是多么欢喜啊。常常一觉醒来觉得心中喜气洋洋,定神一想这喜事原来是又新借到一本书,可以在今天细细读来。那时候很多书都得偷读。有些书得瞒着老师和同学,如被批判过的《苦菜花》、《青春之歌》;有些书连家里人都得瞒,如《红楼梦》,十来岁时读这书毕竟心虚。所以直到今天我读书都有一种偷窃的快乐,读一本好书总有非份而得的暗喜。
十四岁那一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。我报这个系有一种幼稚的想头,我想我不考任何具体的专业,我将来要在图书馆里读遍所有专业的书,我要成为像亚里士多德、罗蒙诺索夫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。入学后当然知道这很虚妄,但我还是兼修了中文、哲学、历史系的课。上大学时年纪小,尚不谙情爱,对班上的爱情事件浑然不觉,谁跟谁的许多故事都是我毕业很久以后才听说的,每每吃惊;当时只知道去图书馆看书。后来考取中文系研究生,加起来共在北大读书十年。我读书很庞杂且不太作计划,读什么书全凭那一时的内心渴望;我相信开卷有益,也相信凡是好书我都早晚得读,与其纳入计划读不如随兴所至地读,我认为书读多了在心中会自然地形成体系。十年勤读完成了我的专业教育,也完成了我的人格教育,我在北大那个小小的湖边了解了世界和古往今来的人生。我知道读书决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的职业活动,实际上读书使我经历了越来越丰富的灵魂生活,赋予我强大的精神力量,使我能够坦然面对那些为世间所贵、所畏的东西。
多少年来,读书成了我生存的基本方式。有时去餐厅吃饭,等菜的功夫我也不由得要到附近的书店买本书来读。现在很多朋友以赚钱为务,这很好;而我安于读书,这也很好。所谓的“时人不识余心乐”,各人有各人的乐趣,各人的乐趣都不足为外人道。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,我很理解,闻道、解惑、得新知的满足是难以言传的。当然我也酷爱旅行,但旅行也算是“读无字书”吧。